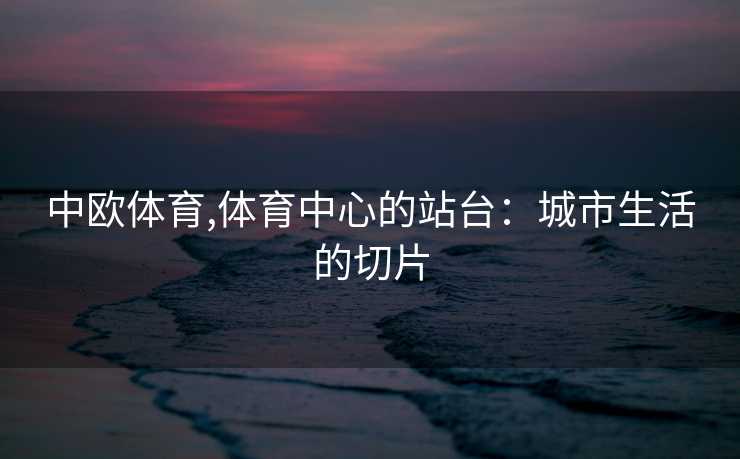清晨六点半,体育中心的站台被薄雾裹着,像块浸了水的海绵。路灯还亮着,橘黄色的光晕洇开,落在候车亭的金属框架上,泛着冷冽的光。卖豆浆的王叔已经支起小推车,蒸汽从保温桶里袅袅升起,混着油条的焦香,撞进早起上班族的鼻尖。“豆浆加蛋还是原味?”他的嗓子带着沙哑,却透着股子熟稔的热乎劲儿。穿西装的小张总爱买原味,边喝边刷手机;扎马尾的高中生则盯着保温桶,眼睛亮晶晶的:“叔,今天有糖糕吗?”王叔笑着掀开盖子,金黄的糖糕冒着热气,惹得旁边等车的阿姨也凑过来:“给我来两个,给孙子带的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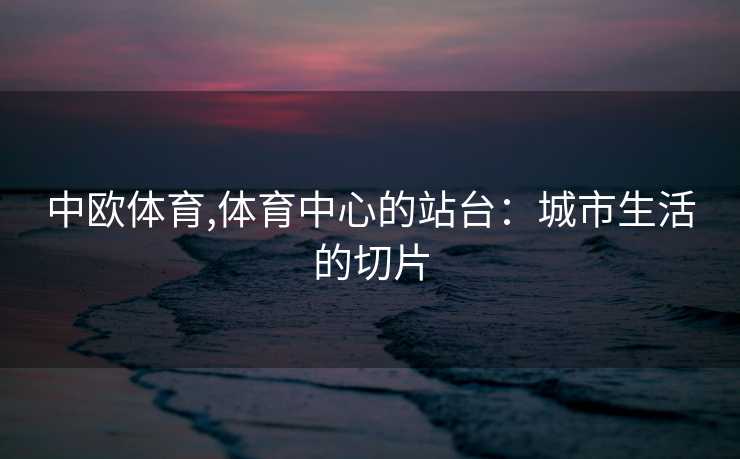
七点的太阳爬上体育馆的屋顶,镀上一层金红。站台边的电子屏滚动着公交线路,人群渐渐多了起来——穿运动服的老人拄着拐杖,耳机里放着戏曲;背着双肩包的大学生低头看地图,眉头皱成小山;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擦身而过,车筐里的餐盒叮当作响。最显眼的是那个穿荧光绿工作服的清洁工,她戴着口罩,手里攥着扫帚,把地面的落叶扫成一堆,又蹲下来捡起烟头,放进随身携带的布袋里。她的动作很轻,像在对待什么易碎的东西。
八点半,人流达到高峰。公交车一辆接一辆驶来,门打开时,人群像潮水般涌上去,又退下来。有个穿校服的女孩被挤得差点摔倒,旁边的阿姨赶紧扶住她,递过一张纸巾:“慢点儿,别着急。”女孩脸一红,说了句“谢谢”,声音细得像蚊子。阿姨笑着拍拍她的背:“我孙女也和你一般大,每次上学都急得跺脚。”这时,一辆载满货物的小货车停在站台旁,司机探出头喊:“麻烦让让,我要卸货!”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,司机感激地点点头,熟练地把货物搬下来,码得整整齐齐。
晌午时分,太阳毒得厉害,站台的长椅被晒得发烫。有人撑着伞站在树荫下,有人把报纸铺在座位上,还有人干脆坐在台阶上,掏出饭盒吃饭。卖凉皮的阿婆推着小车过来,竹筒敲得梆梆响:“凉皮!酸辣粉!”几个工人围过去,一人捧着一碗,吃得满头大汗。阿婆擦了擦额头的汗,笑着说:“慢点儿吃,不够再添。”
傍晚五点,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。放学的小孩蹦跳着跑过来,书包晃得老高;下班的人拖着疲惫的脚步,手里提着菜篮子;情侣们挽着手,靠在站台的柱子上说话。有个穿白衬衫的男人站在那里,手里举着个牌子,上面写着“接女儿”。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下车的人,直到看见穿校服的女孩跑过来,扑进他怀里。男人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,从包里拿出矿泉水:“渴了吧?爸爸给你买了冰淇淋。”女孩咬了一口,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
深夜十点,最后一班公交车驶离站台。空荡荡的候车亭里,只剩下几盏灯亮着。清洁工阿姨又来了,她拿着拖把,把地面擦得锃亮,连角落里的灰尘都不放过。远处的体育馆还亮着灯,隐约传来篮球撞击地面的声音。风掠过站台,吹得广告牌哗啦啦响,仿佛在诉说着这一天的故事。
体育中心的站台,像个沉默的观察者,见证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。它连接着家的方向,也连接着梦想的起点;它承载着平凡的烟火气,也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暖。在这里,每个人都是主角,每个瞬间都值得珍藏。而当新一天的阳光再次洒在站台上时,一切又将重新开始,就像这座城市的心跳,永远鲜活,永远向前。